

我躺在一張白床上,剛剛發生的一切太不真實。床的兩側可以起落把手,不銹鋼的很結實。我還是不能平躺,側身的姿勢配起我軟塌的身型,起身稍顯困難。我抓住把手以它為支點挪蹭我的腿部,才勉強移動到床腳的出口,床沿突出一截,我腳踩不穩地面。「來抱住我,先坐床沿30秒,再起身停30秒,感到穩住了才動。」護工架著我的一側,另一側是我先生的臂膀,我緩緩探到了玻璃隔門外幾步之遙的洗手間。
產後的身體

借著這機會,我停下仔細打量鏡子中的人。她好像沒有什麼變化,還是一身藍花的病號服,毫不貼身地墜著,比劃過一個凸起的梨形。不同的,產後護工給換的這套,花色更新質地更厚,像是提醒著切不可入風著涼。後背的腰痛沒有隨著嬰兒的落地一起娩出,骨盆扭動起來咯咯的生疼依然如影隨形——我只是肚子裡少了一個肉團,讓腰能勉強平躺在床上,以免胎心監測的接觸位置不准。收拾好姿勢後,我忐忑等待著催產素點滴導向的必然痛楚,一邊留心打量著四周。
這裡能一覽所有臨盆的女人,在生產前的狀態和她們的表情。我左側的女人經歷了長久的開指,小聲隱約念著疼痛,她的導樂坐在一旁拍背守著她呼吸。她想要申請先生過來作陪,但終究是沒有。我右側的女人臨產嘔吐,難受得緊了。短暫地,又有推進來一個女人,這次她喊叫很急促,護士圍成一團,內檢後立即推入了生產間。而我前方,那個女人一直在呻吟著催問麻醉師。「八床,八床要不要一起打無痛?麻醉師到了。」她們在問我。
「啊,我要再想想。」我現在還能忍受這一波波的微疼。「麻醉師來一趟,後面再就不知道什麼時候。」「八床,八床的胎心率有異常,胎兒缺氧。」她們很快過來,一位助產士手伸進來用人工破水,就像輕巧捻破一個氣球般,暖流瞬時而出。我便只能躺在隔尿墊上,簡單搭了一條被單。「醫生,我開了幾指?」「兩三指。」我突然有點猶疑,不該這樣,二胎的進程不該這樣緩慢。假如真是跨入了深夜,不打無痛,我如何頂得住疲憊和疼痛的消耗。又細細密密地想着,萬一剛插了管子,麻醉還沒起效就要生了呢?就在那一刻,我意識到原是沒有生娃的孤勇。一胎是太過眷顧,痛是短痛,沒體會到疼痛耗盡。而人一旦把注意力投射到軟處,就感到真的軟弱起來。
熬過六點,先生連續的來電我顧不上,爸爸做的清湯素飯不知何時放在我的床鋪,我已哆嗦得沒法精細地翻開層層飯盒搗鼓勺子,心裡不禁思慮起力氣怎麼頂過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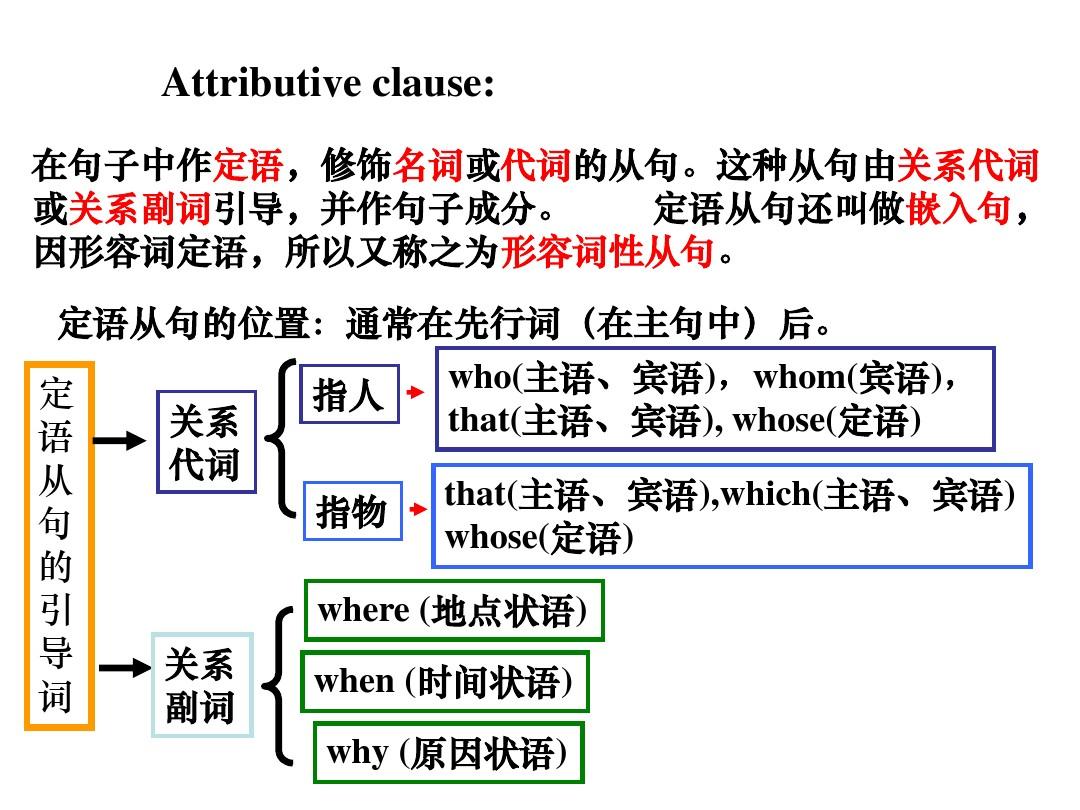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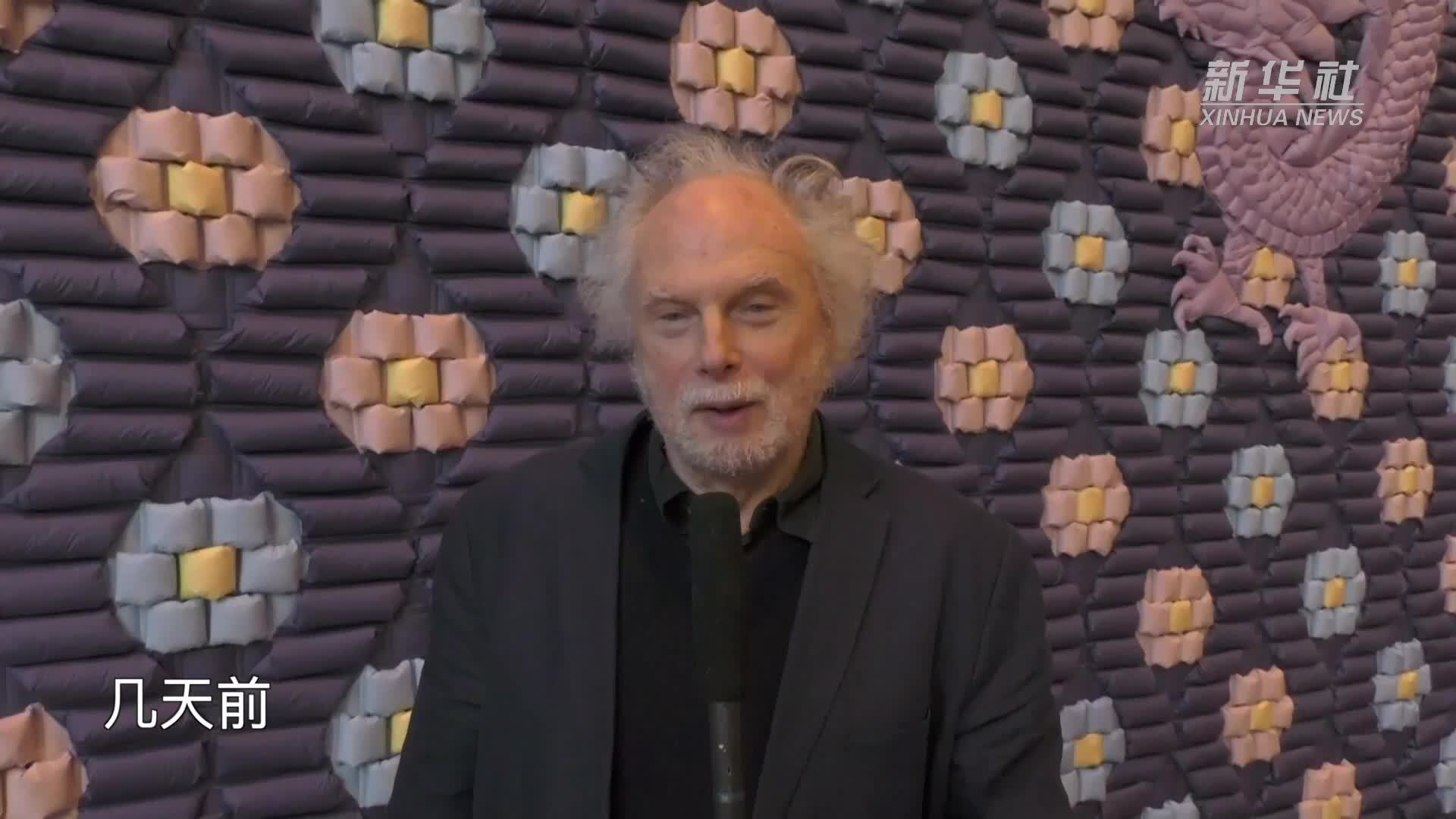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