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作者:詹方歌编辑:邢昀
夏天的傍晚,北京常有火烧云,但对于林司来说,它只在朋友圈铺天盖地,鲜少真切地出现在眼前。身处直播行业,她和大多数人的作息不同:日出是很常见的,有时上早班,有时加班到清晨,太阳总会规律地跃出地平线。可晚场直播是午后上班,凌晨下班,刚好错过日落。
这像是一种有关日不落的隐喻——哪怕身在行业里的人已经感受到明显的寒意,但无论从直播企业的财报数字、品牌的投放还是平台数据,都还看是积极向好。诸多从业者的叙述中,2023年仍是直播行业的辉煌顶峰,不少直播间GMV飙高,平台处在用户转化的高增长时期,从业者也一度被认为是高薪的代表。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,2023年直播市场规模达2095亿,较2022年增长5.15%。这样的图景在当下的就业环境里独树一帜。
也因此,即便快节奏、高强度、精神亢奋、昼夜颠倒,直播行业仍旧吸纳着大量年轻人。2024年,情况开始从细微处变化:新入行的年轻人薪资明显比之前更低、主播竞争加剧、直播间退货率大幅提升……直播上市企业2024半年报里,仍保持着高增长的叙述,日不落的直播间里,狂欢似乎还在继续,但如果你把这些数字讲给诸多从业者,他们几乎难以置信。
几万和五千
一天赚几万,对我来说是很常规的事情。克里说。和所有你能想到的行业一样,直播带货的行业群体也是金字塔形,克里的收入至少在颈部以上。他做明星助播,GMV最高的一场有13亿元,从业不到四年已经开了自己的公司,每月工作十天到半个月不等,月收入稳定在6位数。在他的圈子里,这收入不算高也不算低。
李卷做达人助播,在两年间尝试了五六份直播工作以后,她终于决定不再服务于任何公司,只跑直播场次,同时放弃提成,只拿固定时薪。每天跑两场,每场大概7小时,算下来月收入有小两万,和做房产销售的时候差不多。
孙檬今年刚刚大学毕业,进了深圳的直播公司做带货主播,和克里一样,她一场直播的时间大概是7到8个小时,晚上一、两点下班是常事,每场直播的GMV只有4000块左右,她的月薪在5000到6000元之间。
巨大的薪资差异来自很多重因素,比如地域、公司,甚至天赋。但最重要的是时机。克里告诉《豹变》,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四年间,直播行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,竞争也越来越激烈。孙檬的专业是传播与策划,大部分课程落在直播上。但当她走出大学,当年的热门行业已经变了天。
我要是早毕业两年更好。克里的评价很直接。他2020年入行,见过太多从草根一路走上人生巅峰的带货主播。2016年到2018年间,行业资源和资本还集中在秀场和游戏直播,带货远远没成为主流商业模式,一些灵敏嗅到风口的年轻人已经入局。李佳琦、薇娅的起点都是2016年的淘宝。在2019年站上风口的大主播们,成为离流量和钱最近的一批人。当时的直播带货,被认为是来钱最快的职业。
就连锤子手机创业失败的罗永浩,都在次年4月宣布用直播带货的方式还债。不过,来钱快的角色,其实只是主播。搭建起一个直播间,至少还需要运营和摄像。运营操控着直播带货过程中的所有的策略,承担大脑的角色。北京某知名直播间,在行业内以薪资福利差著称,给新人运营的普遍薪资是每月八千元,即便做出过千万GMV(商品成交总额)的大型直播场次,收到的提成也只有每月三千元,还是行业总体不错的2023年。今年情况更差,几乎拿不到提成。摄像和递品的工作最为基层,不少由实习生完成,一天150元,流动率大到正式员工记不清他们的名字。
事实上,金字塔的描述不够准确。如果说直播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风口,不断涌入的年轻人则形成了一座流动的沙丘。风吹过,不断有新的砂砾翻起,也有更多的砂砾被堆积到底部——你或许还记得薇娅是谁,而底部挣扎如孙檬,仅限于原地打转,看不到向上的路径。
是围城,更是茧房


这一行是没人教的。从克里和李卷入行时就是。
2021年,克里在直播公司的培训就是半小时的台词背诵。进入直播间后,他开始学习各种话术和禁忌词,以及如何吸引用户的注意力。李卷则进入了另一个直播间,以助播的身份被要求重复说一句话,足足一整天。
这个行业入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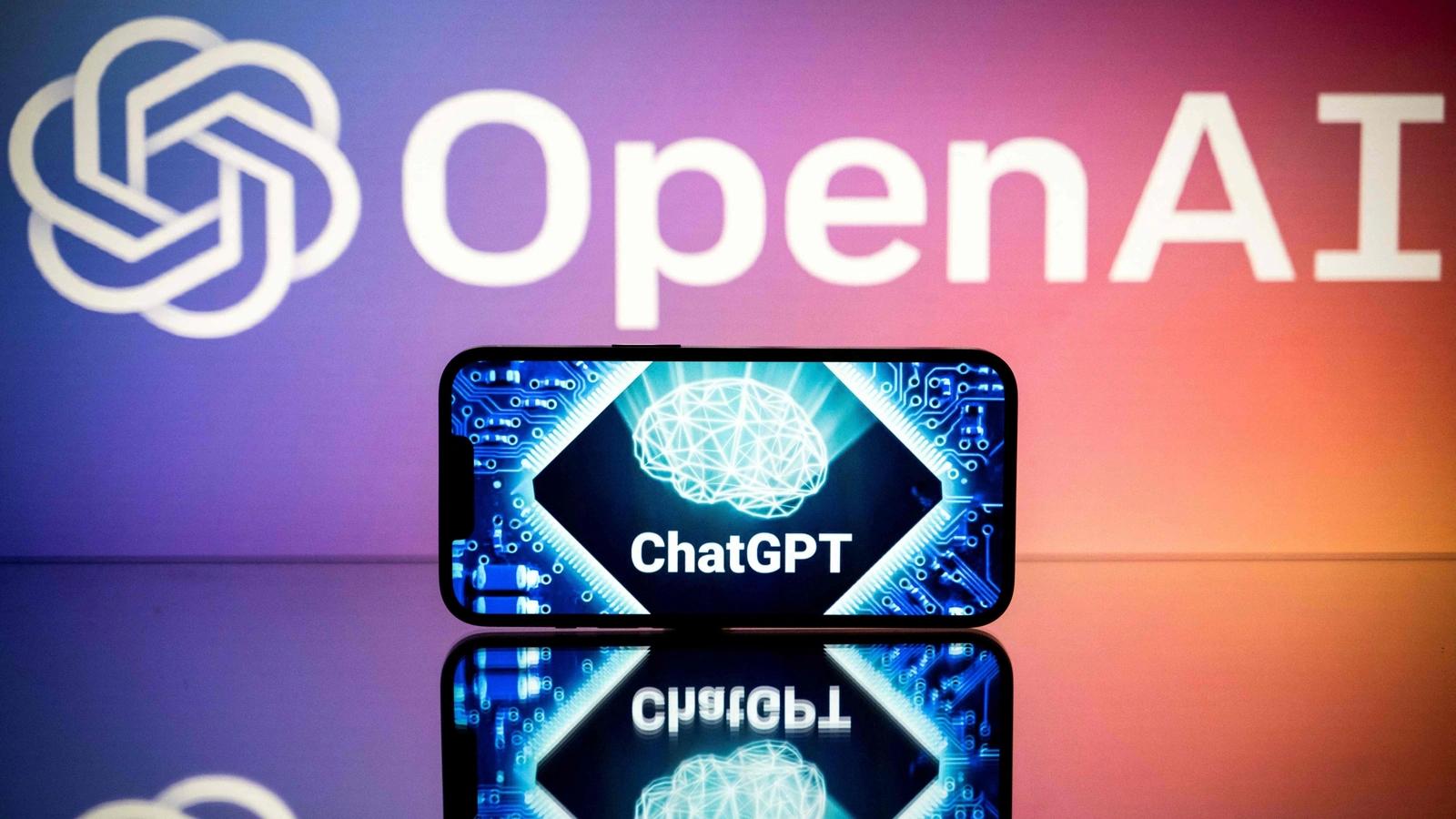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