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我躺在一张白床上,刚刚发生的一切不太真实。床的两侧可以起落把手,不锈钢的很结实。我还是不能平躺,侧身的姿势配起我软塌的身型,起身稍显困难。我抓住把手以它为支点挪蹭我的腿部,才勉强移动到床脚的出口,床沿突出一截,我脚踩不稳地面。「来抱住我,先坐床沿30秒,再起身停30秒,感到稳住了才动。」护工架着我的一侧,另一侧是我先生的臂膀,我缓缓探到了玻璃隔门外几步之遥的洗手间。
医生中午内检时宫颈已经软化开口,水囊总是免了。
待产房

两点,我准时到达待产房。待产房这里的周遭,我感到新鲜而陌生。床头高架挂着催产素瓶子,整个下午护士来来去查看胎监数据,每次顺便将滴漏又加大一码。我垫着一个三角斜坡状的长条软枕,让腰能勉强平躺在床上,以免胎心监测的接触位置不准。收拾好姿势后,我忐忑等待着催产素点滴导向的必然痛楚,一边留心打量着四处。
这里能一览所有临盆的女人,在生产前的状态和她们的表情。我左侧的女人经历了长久的开指,小声隐约念着疼痛,她的导乐坐在一旁拍背守着她呼吸。她想要申请先生过来作陪,但终究是没有。我右侧的女人临产呕吐,难受得紧了。短暂地,又有推进来一个女人,这次她喊叫很急促,护士围成一团,内检后立即推入了生产间。而我前方,那个女人一直在呻吟着催问麻醉师。

人工破水
「八床,八床要不要一起打无痛?麻醉师到了。」她们在问我。「啊,我要再想想。」我现在还能忍受这一波波的微疼。「麻醉师来一趟,后面再就不知道什么时候。」「八床,八床的胎心率有异常,胎儿缺氧。」她们很快过来,一位助产士手伸进来用人工破水,就像轻巧捻破一个气球般,暖流瞬时而出。我便只能躺在隔尿垫上,简单搭了一条被单。
犹豫
「医生,我开了几指?」「两三指。」我突然有点犹疑,不该这样,二胎的进程不该这样缓慢。假如真是跨入了深夜,不打无痛,我如何顶得住疲惫和疼痛的消耗。又细细密密地想着,万一刚插了管子,麻醉还未起效就要生了呢?就在那一刻,我意识到原是没有生娃的孤勇。一胎是太过眷顾,痛是短痛,没体会到疼痛耗尽。而人一旦把注意力投射到软处,就感到真的软弱起来。
导乐的帮助
熬过六点,先生连续的来电我顾不上,爸爸做的清汤素饭不知何时放在我的床铺,我已哆嗦得没法精细地翻开层层饭盒捣鼓勺子,心里不禁思虑起力气怎么顶过天明。我预约的导乐来得非常及时。她握着我的手,让我缓缓坐起来。她帮忙褪去我的袜子,裹好我的被单,招呼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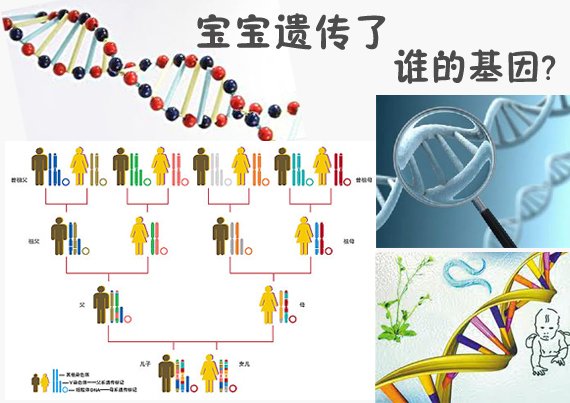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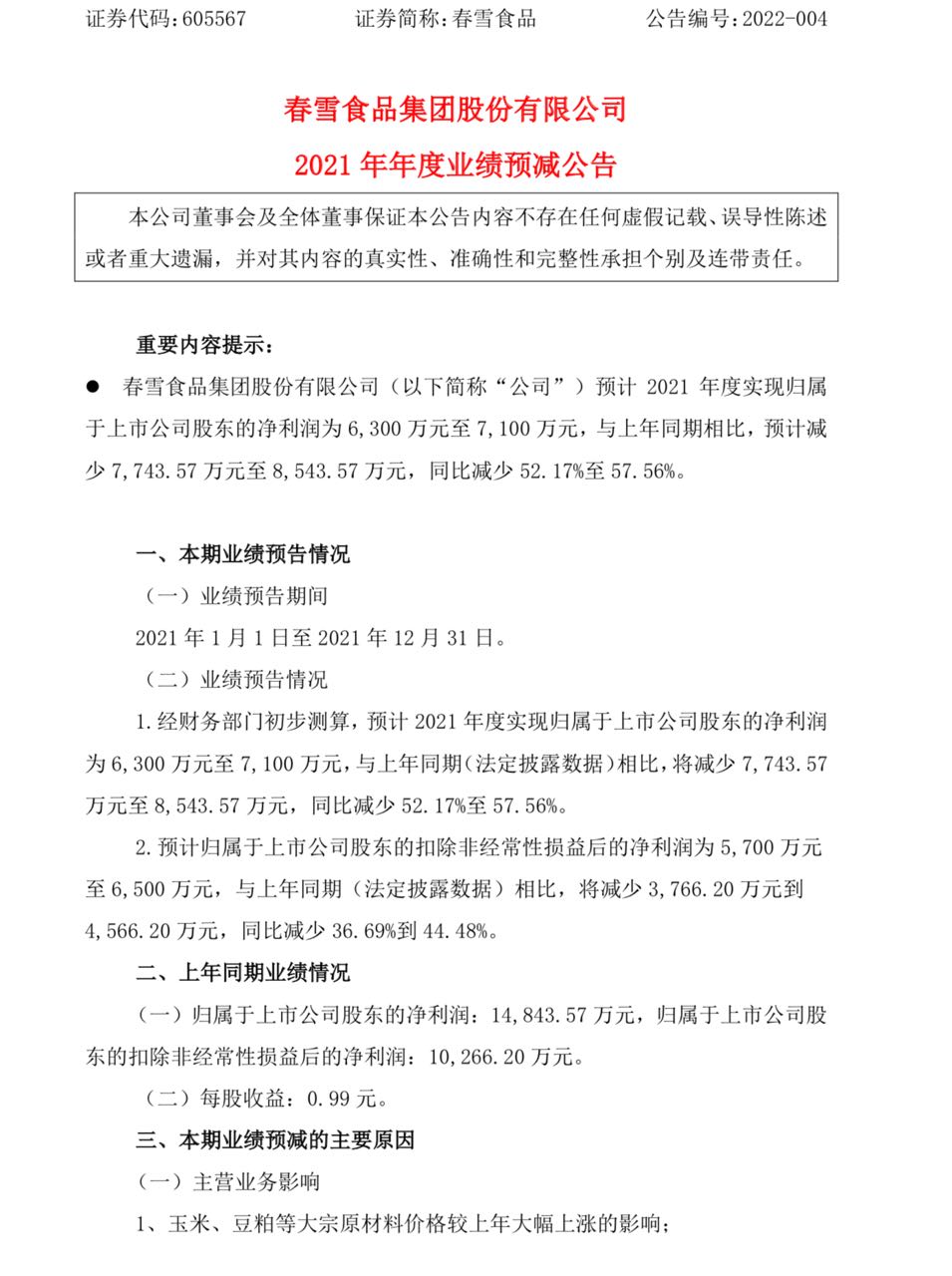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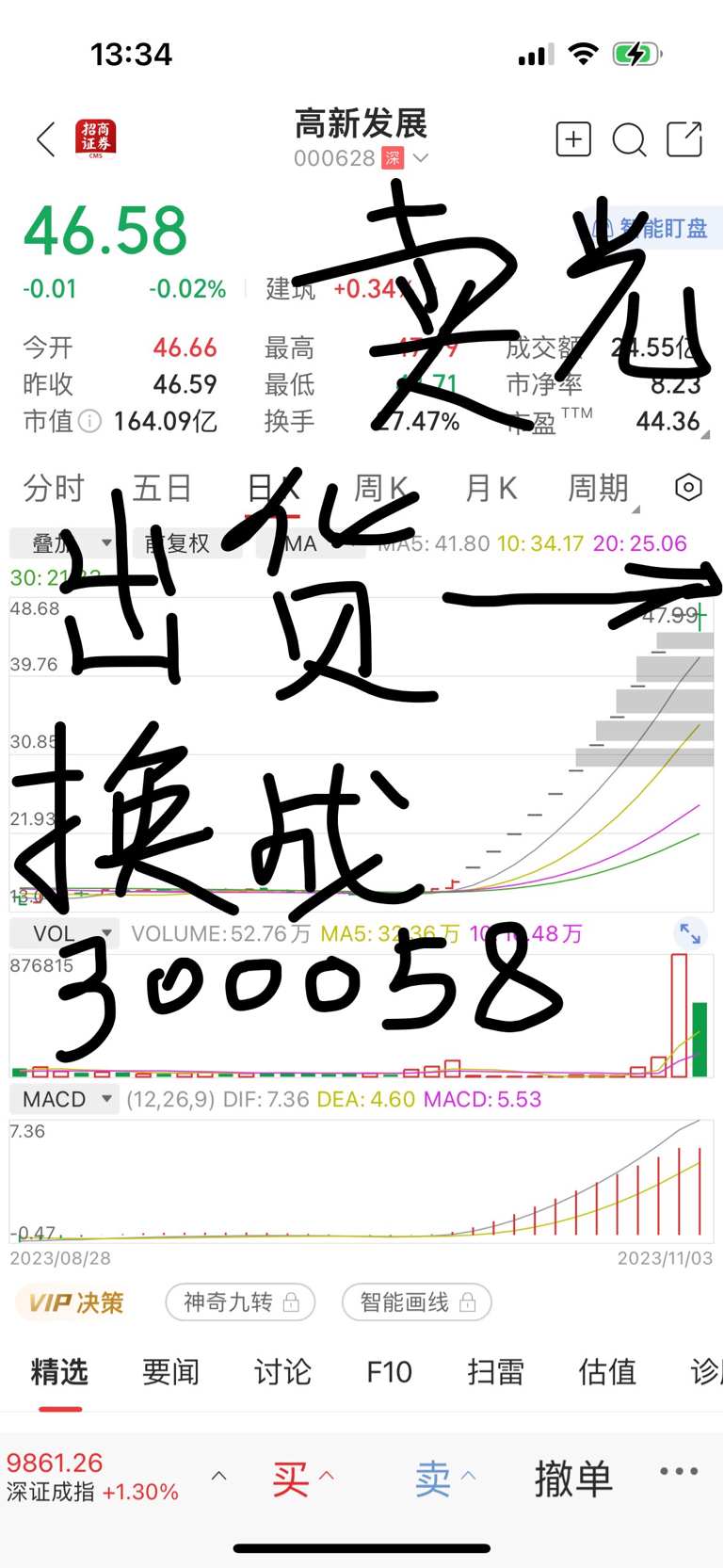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